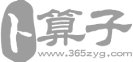易經(jīng)入門學(xué)習(xí)—誠信,《易》之大者
子曰:“人而無信,不知其可也,大車無輗,小車無軏,其何以行之哉?”孔子之言,歷經(jīng)千年,今日道來,仍然振聾發(fā)聵。誠信是人與人之間交往的基石,所以作為五經(jīng)之首、大道之源的《易經(jīng)》尤其注
“孚”,誠也,信也。《周易》六十四卦中,有二十五卦言“孚”,有“孚”字40處,其中上經(jīng)13處,下經(jīng)27處。如第五卦《需》卦辭“有孚光,亨,貞吉,利涉大川”,狩獵以需,需要彼此間有誠信,團結(jié)合作,戰(zhàn)勝困難,而且狩獵以需,需要結(jié)盟增加力量,而結(jié)盟更需要誠信,否則哪有可能結(jié)盟,就是結(jié)盟也是各懷鬼胎,起不到盟友之間真誠相幫的作用。第六卦《訟》卦辭“有孚,窒惕,中吉,終兇,利見大人,不利涉大川”,訴訟之時,亦應(yīng)有誠信,才利于去見王公貴族,團結(jié)內(nèi)部力量,以贏得訴訟之勝。第八卦《比》初六爻辭“有孚,比之,無咎;有孚,盈缶,終來有它吉”,要親比,彼此必須有誠心,如果有誠心如瓦罐美酒滿盈,最終會有親附,可見周公對誠信的看重。第九卦《小蓄》六四爻辭“有孚,血去惕出,無咎”,誠信才可以避免受到傷害。《小蓄》九五爻辭“有孚攣如,富以其鄰”,以誠信建立聯(lián)系,富而影響到它的近鄰,這樣才可以逐漸小蓄力量,慢慢得以強大。第十一卦《泰》,必有“孚”,有“孚”方“泰”也,“勿恤有孚,于食有福”。第十七卦《隨》,隨必有孚也,為人臣必忠信隨于君也。第二十卦《觀》卦乃講武王孟津之誓,觀諸侯反應(yīng),因此必講有“孚”,亦觀諸侯之“孚”也;第二十九卦《坎》,坎為險,居險之時,有“孚”方可脫險也。
下經(jīng)自第三十四卦《大壯》始,《大壯》雖講戰(zhàn)爭,然戰(zhàn)爭必齊心協(xié)力,故言“征兇,有孚”;接著《晉》卦(第三十五卦)亦講戰(zhàn)爭策略,康侯蕃馬,王母鼓士氣,戰(zhàn)爭策略是不用講誠信的,故曰“罔孚”;第三十七卦《家人》卦,治家之時,需講誠信,才能有威信,有威嚴,否則,對家人不講誠信,沒有信用,誰會信任你呢,家人之間失去信任,那會是什么樣的結(jié)果?所以周公對治家,強調(diào)誠信,才能“威如”,雖然可能一時不為家人理解,可最終一定能夠理解的。第三十八卦《睽》卦,彼此以誠信相交,才化解了危險沖突,最終“厲無咎”,故“睽”亦有“孚”。第四十卦《解》,有“孚”方可“解”也;第四十一卦《損》,損上必有孚,方為臣下服;第四十二卦《益》亦如《損》也;第四十三卦《夬》,下決心豈能無“孚”?第四十四卦《姤》,姤,遇也,無“孚”豈能相遇?第四十五卦《萃》,萃,聚也,相聚必誠,故“萃”必有孚;第四十六卦《升》,升而南征,眾志誠志,豈能無“孚”?第四十八《井》卦,有孚方可治國以修井田也;第四十九《革》卦,革必有“孚”方能成功也;第五十五卦《豐》卦雖言戰(zhàn)爭,可必須有“孚”,以凝聚人心,故《豐》六二“豐其蔀,日中見斗,往得疑疾,有孚發(fā)若,吉”;第五十九卦《渙》卦言天下渙散之時,君王必要大刀闊斧,要有魄力,“渙其群”而為“渙有丘”,因而不用言“孚”;第六十一卦《中孚》自然有孚也;第六十四卦《未濟》,天下尚未成功,同志仍需努力,故有“孚”也。《未濟》作為六十四卦的最后一卦,三提“有孚”,其意深遠,圣人對后世之誡,幾微致遠矣。
易經(jīng)入門學(xué)習(xí)
誠信之重要,不僅《周易》崇尚,古之圣賢莫不重之,舜命禹伐三苗時,三旬苗仍逆命,最后亦是以誠感動三苗來服。
春秋五霸之一齊桓公因雖為魯國曹劌(guì)之逼,然聽從管子之勸,信守承諾,以幾百里土地而讓天下人皆知桓公之誠信,最終得以九合諸侯,一匡天下。
春秋五霸之一晉文公重耳亦注重誠信,使其逐漸成就霸業(yè)。如民未知信之時,重耳伐原以示之信,對此《左傳》載其言曰“信,國之寶也。”以信得民心,以信得軍心,以信救饑,文公而霸,不亦宜乎?
《管子》云“非誠賈不得食于賈,非誠工不得食于工,非誠農(nóng)不得食于農(nóng),非信士不得立于朝。”“臨事不信于民者,則不可使任大官。”
《禮記.儒行》:“儒有不寶金玉,而忠信以為寶。”

《禮記.大學(xué)》: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國;欲治其國者,先齊其家;欲齊其家者,先修其身;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;欲正其心者,先誠其意;欲誠其意,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,物格而后知至,知至而后意誠,意誠而后心正,心正而后身修,身修而后家齊,家齊而后國治,國治而后天下平。”又云“《詩》云:"穆穆文王,于緝熙敬止!"為人君止于仁,為人臣止于敬,為人子止于孝,為人父止于慈,與國人交止于信。”其說和《周易》尚“誠信之孚”一脈相承。
《中庸》云“自誠明,謂之性。自明誠,謂之教。誠則明矣。明則誠矣。唯天下至誠,為能盡其性;能盡其性,則能盡人之性;能人之性,則能盡物之性;能盡物之性,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;可以贊天地之化育,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其次致曲。曲能有誠,誠則形,形則著,著則明,明則動,動則變,變則化。唯天下至誠為能化。至誠之道,可以前知。國家將興,必有禎祥;國家將亡,必有妖孽。見乎蓍龜,動乎四休。禍福將至:善,必先知之;不善,必先知之。故至誠如神。”其《易》之“孚誠”之謂乎?
《荀子》曰“君子養(yǎng)心莫善于誠,致誠則無它事矣。惟仁之為守,惟義之為行。誠心守仁則形,形則神,神則能化矣。誠心行義則理,理則明,明則能變矣。變化代興,謂之天德。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,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,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。夫此有常,以至其誠者也。君子至德,嘿然而喻,未施而親,不怒而威:夫此順命,以慎其獨者也。善之為道者,不誠則不獨,不獨則不形,不形則雖作于心,見于色,出于言,民猶若未從也;雖從必疑。天地為大矣,不誠則不能化萬物;圣人為知矣,不誠則不能化萬民;父子為親矣,不誠則疏;君上為尊矣,不誠則卑。夫誠者,君子之所守也,而政事之本也,唯所居以其類至。”
《呂氏春秋》亦云“君臣不信,則百姓誹謗,社稷不寧;處官不信,則少不畏長,貴賤相輕;賞罰不信,則民易犯法,不可使令;交友興主,則離散郁怨,不能相親;百工不信,則器械苦偽,丹漆染色不貞。夫可與為始,可與為終,可與尊通,可與卑窮者,其唯信乎!信而又信,重襲于身,乃通于天。以此治人,則膏雨甘露降矣,寒暑四時當矣。”
易經(jīng)入門
黃石公《兵家三略》亦云“將無還令,賞罰必信,如天如地,乃可御人”。
國君之誠信,有時事關(guān)國家安危。晚唐之時,因唐德宗賞賜未兌現(xiàn)于將兵而致“涇師之變”,故《新唐書.陸贄傳》載陸贄勸諫唐德宗曰“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,又有懼溺而自沈者,其為防患,不亦過哉!愿陛下鑒之,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。臣聞人之所助在信,信之所本在誠。一不誠,心莫之保;一不信,言莫之行。故圣人重焉。傳曰:"誠者,物之終始,不誠無物。"物者事也,言不誠即無所事矣。匹夫不誠,無復(fù)有事,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,而可不誠于人乎?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,臣竊非之。孔子曰:"可與言而不與之言,失人;不可與言而與之言,失言。智者不失人,亦不失言。"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,可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。所謂民者,至愚而神。夫蚩蚩之倫,或昏或鄙,此似于愚也。然上之得失靡不辨,好惡靡不知,所秘靡不傳,所為靡不效。馭以智則詐,示以疑則偷;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,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。上行則下從之,上施則下報之,若景附形,若響應(yīng)聲。故曰:"惟天下至誠,為能盡其性。"不盡于己而責(zé)盡于人,不誠于前而望誠于后,必紿而不信矣。今方鎮(zhèn)有不誠于國,陛下興師伐之;臣有不信于上,陛下下令誅之。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,以陛下所有責(zé)彼所無也。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己。愿陛下慎守而力行之,恐非所以為悔也。”
易經(jīng)學(xué)習(xí)
《愛蓮說》之作者、宋代易學(xué)大家周敦頤亦對“誠”有精辟的論述,其《通書》云:“誠者,圣人之本。大哉乾元,萬物資始,誠之源也。乾道變化,各正性命,誠斯立焉,純粹至善者也。故曰:一陰一陽之謂道,繼之者善也,成之者性也。元亨,誠之通;利貞,誠之復(fù)。大哉《易》也,性命之源乎!圣,誠而已矣。誠,五常之本,百行之源也。靜無而動有,至正而明達也。五常百行,非誠非也,邪暗塞也,故誠則無事矣。至易而行難,果而確,無難焉。故曰:一日克己復(fù)禮,天下歸仁焉。誠無為,幾善惡,德愛曰仁,宜曰義,理曰禮,通曰智,守曰信;性焉安焉之謂圣,復(fù)焉執(zhí)焉之謂賢,發(fā)微不可見、充周不可窮之謂神。寂然不動者,誠也;感而遂通者,神也;動而未形、有無之間者,幾也。誠精故明,神應(yīng)故妙,幾微故幽。誠、神、幾,曰圣人”。
司馬光之《資治通鑒》亦曰:“夫信者,人君之大寶也。國保于民,民保于信。非信無以使民,非民無以守國。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,霸者不欺四鄰,善為國者不欺其民,善為家者不欺其親。不善者反之:欺其鄰國,欺其百姓,甚者欺其兄弟,欺其父子。上不信下,下不信上,上下離心,以至于敗。所利不能藥其所傷,所獲不能補其所亡,豈不哀哉!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,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,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,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。此四君者,道非粹白,而商君尤稱刻薄,又處戰(zhàn)攻之世,天下趨于詐力,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,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!”
《忍經(jīng)》所謂“自古皆有死,民無信不立,尾生以死信而得名,解揚以承信而釋劫。范張不爽約于雞黍,魏侯不失信于田獵。”與《易》之注重誠信,其意一也。